悲情城市 (A City of Sad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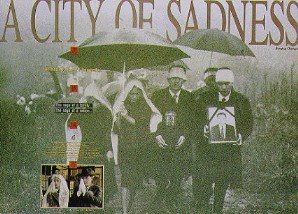 「二二八事件」,難免是台灣老一輩的民眾心裏的一道傷痕。1947 年2月27日的台北市,一名販賣私煙的婦人被警員打至重傷,激發起一直不滿當時還在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群眾內心的怒火。28日,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觸發了台灣各地原居民對政府的抗爭。最後,蔣介石從大陸調派軍隊到台灣進行鎮壓,過程中約有二萬名台灣人被屠殺。
「二二八事件」,難免是台灣老一輩的民眾心裏的一道傷痕。1947 年2月27日的台北市,一名販賣私煙的婦人被警員打至重傷,激發起一直不滿當時還在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群眾內心的怒火。28日,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觸發了台灣各地原居民對政府的抗爭。最後,蔣介石從大陸調派軍隊到台灣進行鎮壓,過程中約有二萬名台灣人被屠殺。台灣導演侯孝賢以「二二八事件」作為《悲情城市》的背景,道出這件悲劇對當時台灣的平民百姓做成何等的創傷,以及台灣原居民的身分認同問題。侯孝賢亦是憑《悲情城市》,揚威於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
故事以林姓一家為中心。大哥文雄經營酒家,二哥文森到南洋打仗後一去不回,三哥文良在戰爭後精神失常,而最細的兒子文清 (梁朝偉 飾) 為聾啞人仕,以攝影為事業。
電影從1945 年日軍投降,中國 (國民黨) 政府收回台灣時展開序幕。導演在片的初段表現了這段時期台灣民眾的矛盾心情,他們一方面對回歸祖國充滿憧憬,另一方面亦對那些早已結下微妙感情的日本朋友及文化的離去懷有依依不捨之情。片中少女插花的片段以及當地知識分子對於日本民族精神的談論,都可顯出當時的台灣人其實頗崇尚日本「美」的一面。相反,基於文化及生活上的差異,縱然是同一個民族,台灣原居民及從中國內地到台灣的人(外省人)之間的分歧卻更加大。
片中角色間的對話已交待出因此而洐生的社會問題。中國人不信任台灣原居民,認為他們被日本「奴化」而將他們拒於公職門外。另一方面,官員的貪污及走私問題卻相當嚴重,致使當時台灣原居民的生活比日治時期更差,他們對政府的不滿亦由此而起。而片中林家大哥文雄與上海人的交談需要經過多種語言的傳譯,亦突顯出原居民及外省人之間的隔膜。文雄的一句「咱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甚麼日本人,一下甚麼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沒人疼。」,實在令人反思。身分認同的問題,會否就是台灣人不斷爭取獨立的原因呢?
對於「二二八事件」,導演並無作出直接的描繪,只以政府在電台的廣播以及角色間的談論對形勢作出交待。電影的重點,始終是在於事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及人心的打擊。對政治犯的屠殺,電影亦只是以獄中的槍聲作表達,反而一個拍下監獄內長長的走廊中四弟文清被獄卒押走的固定鏡頭,更能帶出對回歸的憧憬跌入無盡深淵的感覺。導演對事件作出淡化的描寫,無疑是為了令觀眾對此作出更冷靜及客觀的反思。
梁朝偉在《悲情城市》的演出令人佩服,沒有任何說話,他全憑面部表情及身體語言把一切情感表達出來。話說回來,其角色的不能言,亦似乎象徵了當時台灣人在強權下不敢言的苦況。另外,我亦終於見識到導演侯孝賢愛用的固定遠距鏡頭 (這是我第一次看侯孝賢的作品),除了捕足角色,鏡頭還捕足了台灣九份的風貌,帶著一份難以形容的美感。電影的主題音樂,亦跟電影本身一樣難忘。
連載於光影之下




0 Comments:
發佈留言
<< Home